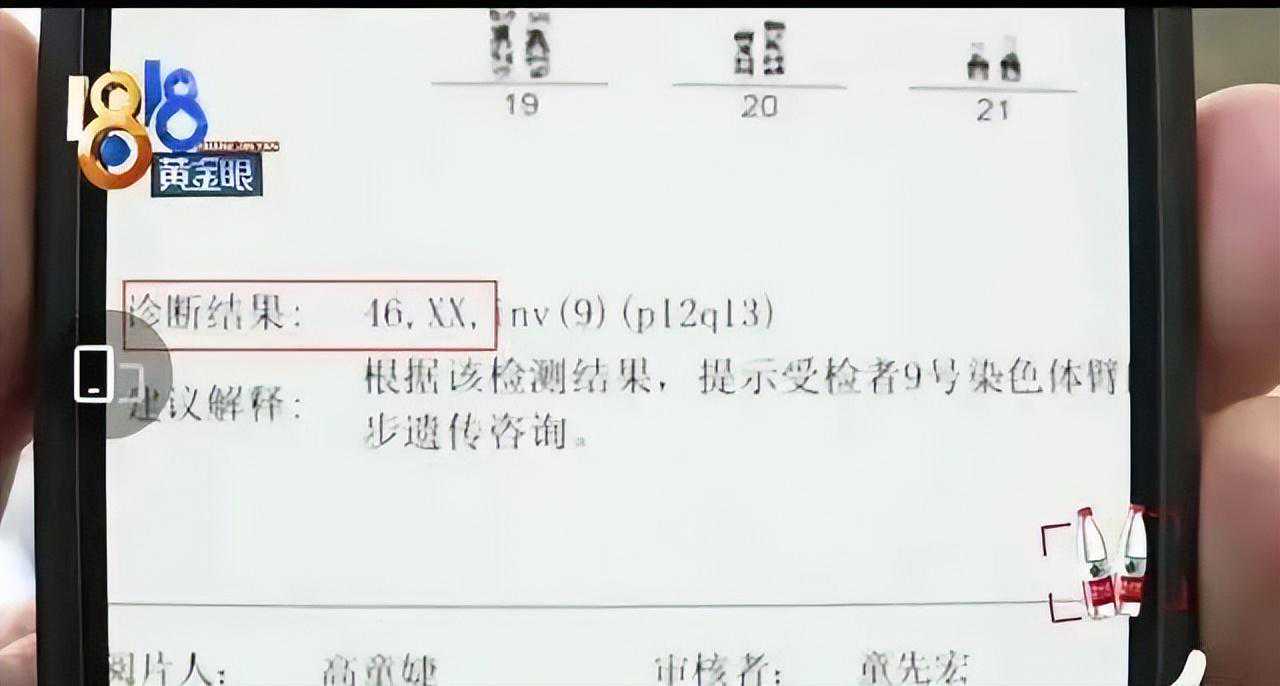阴历九月初六、阳历十月一日,选择这一天,为父母合灵,送父母最后一程。
秋风萧瑟、天阔人稀、田野寂寥、心情低落。
从家族坟地回到家中,家人的心情还没有恢复过来,我也是。
这一次相聚,是三年来家族人数最齐的一次,上一次还是大外甥结婚的时候。
也许是最后一次了,父母不在了,家乡就成了故乡了,想想都心痛。
父母亲一个1936年人、一个1937年人,倏忽80多年已经过去了,如今入土为安,融入这片土地,属于他们的鲜活生动经历、酸甜苦辣的故事,今后只存在我们儿女的记忆中了。
我们活着的时候,还记得他们的生活点滴。
三五十年后,我们不在时,孙辈、重孙辈们是否还记得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?
环顾空荡荡的,2003年时我的婚房,看到那张备料20年、表老80多岁拖着病躯、精心打制的婚床,不禁悲从中来。
睹物思人,老实厚道、重视礼节的家父和街北头慷慨好义、技艺纯熟的木匠高表老半个多世纪的友情点滴,一幕幕晃入眼前.
1.那些年,逢年过节,我们爷俩都要给大郭庄的木匠高表老家送节礼
小时候家穷、人口多,平时吃得差,即便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,也就只能粗茶淡饭、吃个盐豆子、咸菜,混个肚儿圆,于是每年逢年过节,放开肚皮吃点好东西,就成了一天天的期盼。
立秋一过,天气转凉,肚子里的馋虫就泛起来了,春节还太远,中秋节就是焦灼等待的唯一期盼了。
老家一直称呼“八月十五”,这个日期,对儿时嘴馋的我,一直是数着天盼来的。
不仅“八月十五”当天,全家可以坐下来吃月饼、咸鸭蛋、猪肉,节日之前一些天,我跟着父亲各家送节礼时,也能提前吃点好东西。
现在仍然记得,那些年的中秋节和春节,父亲带着我,爷俩一起各处送节礼的情形,尤其是去大郭庄,三节两寿,次次都去。
我奶奶的娘家也在大郭庄,我父亲带着去,除了去两个舅姥爷家送节礼外,木匠高表老家也是每年必去的。
老家80年代初,街面上的物资还是比较缺乏的,送节礼的果品就是老几样:三刀、角蜜、金果棒、芙蓉、桃酥等,中秋节和春节当天,配上四包传统果子、再拎上几斤猪肉、几条父亲早几天打的鱼、几斤酒,他就摇摇晃晃的带我上路了。
父亲代表我爷爷奶奶,到他两个舅家送节礼,人之常情,可以理解。
可为什么要去那庄里的木匠表老家呢?
表老、表老,一表三千里,他究竟算我们什么样的亲戚呢?
我小时候,曾多次问过父亲,家里这么穷,好东西自己吃不香么?为什么送给表老?他只是笑笑不语。
后来我长大了,才知道,故事还得1948年说起。
2.父亲送豆腐被扣在了地主大院
解放前,为躲避国军抓壮丁、也为了赚外路的活钱养家糊口,我爷爷关了街里的铁匠铺子,一个人跑到徐州、枣庄、蚌埠、济南等地谋生,挣点钱就朝家里寄。
家里我祖奶奶当家,带着我奶奶和一大家老少勉强度日,我们家男丁少,还免不了受人欺负。
我爷爷不在家时,父亲十一二岁半大孩子,就不得不学着帮家里干活了,田里捡拾秋剩、河边下网逮鱼、街里帮人跑腿,有活就干,给人帮忙后,顺带总带点饭菜回家,帮衬着家里八九张嘴。
1948年10月中旬,我父亲按约定给曹家地主大院送新做好的几板豆腐,结果一去就没让回来。
当时国共两军对垒,正是淮海战役前夕,碾庄被围了起来,街面上风雨欲来、气氛肃杀。
曹八集圩墙内地主云集,一直是国军地盘,当时几大地主大院都被征用,曹八集小学被用作第44师师部,国军在刘声鹤师长的带领下,征召圩里的所有人,参与修筑工事,准备负隅抵抗。
可怜我送豆腐进去的父亲,被抓了正着,送进了豆腐、人也出不来了,在地主大院做了苦力。
挖壕沟、抬麻袋、做馒头、刷锅烧火..连着十几天不眠不休,把身体彻底累垮了,他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,讲话有点结巴,也是被当兵的用枪托子吓的。
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碾庄战斗开始前,首先扎紧的是防止黄百韬兵团西撤入徐州的曹八集(现在的八义集)的口袋。据老辈们说,国共两党在八义集老街内外交战时,圩墙内外血流成河、尸体都来不及抬。
由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,加上守城国民党火力强大,十三纵的前两次攻入圩子,均被扼杀在城里了。
直到第二天下午,十三纵大部队果断发动总攻,才以高昂的牺牲,最终占领了曹家炮楼,拔掉了东陇海线的邪恶钉子,使解放军在整个战场重新占据了主动权,从而为淮海战役走出胶着状态奠定了基础。
3.父亲爬出了麻袋包
在攻打曹八集战况最激烈的两天时间里,父亲被困在圩里,没法脱身,守军让他跑前跑后给搬运子弹箱子、麻袋工事,枪子掠着头皮就飞过去了。
当时,虚岁十二的父亲又累又饿、又怕又慌,多亏当时地主大院里曹姑奶和街北头木匠高表老的不时照顾、给点吃的、好言安慰,才稳定了心神。
那时,两位二十出头的“大人”只是认识常在街面上跑动的这个石家小孩,对他并不熟悉,紧急情况下,对他的照顾,是天然的悲悯之心和朴素情怀,而年幼的父亲,也就把这两个当时还陌生的“大人”作为了依靠。
曹姑奶和高表老可怜我父亲这半大的孩子,他们知道子弹不长眼睛,两人一商量,就把我父亲给埋在了工事旁的麻袋包里,捅了几个窟窿眼,让他蜷缩在那里,一动别动。
父亲哆哆嗦嗦地躺在麻袋包里,大气不敢喘,就听见整夜都是枪声、炮声、惨叫声,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,弹片贴着他的耳朵飞驰而过,褴褛的衣服吓得干了又湿、湿了又干,灵魂都出吓得出窍了。
直到1948年11月11日下午,坚固的圩墙破了,父亲被高表老扒拉出来时,面无血色、腿都站不稳了,听到枪声停了,看见身边军人衣服不一样了,才知道死里逃生、躲过了一劫。
此后,逢年过节,父亲都要去曹姑奶和街北头的木匠高表老那走动、答谢他俩的救命之恩。
几包礼品,虽不是涌泉相报,但父亲也尽其所能,常年累月地表达着自己朴素的心意。
4.爷俩半辈子的感情
那些年给高表老和曹姑奶送节礼,我不能走路的时候,父亲背着我去;
我能走路的时候,父亲拎着我去;
等我上小学时,就和父亲一起推着礼物去大郭庄了。
我很喜欢去高表老家送节礼,因为老头和蔼可亲、爱开玩笑,喜欢孩子。
每次去,他家的零食都招待我吃得饱饱的,有时,我们送的礼没有我吃下去得多。
对于父亲每年两次的节礼、风雨无阻、坦诚谦恭,高表老挺感动的,我们爷俩去时,他都会早早地等在村口,混浊的眼神闪着亮光。
老爷子干了一辈子木匠,徒子徒孙遍布各庄,真不缺吃的喝的,但他被父年年逢年过节送礼的周到礼仪感动了,他认定了我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厚道人,对我父亲也格外的好。
他爷俩原本有个计划,我上学如果上不成的话,就跟着他儿子、在县里开家具店的那个三叔学木匠,这在农村能安身立命,肯定比种地强。
后来我考上大学了,高表老很高兴,但也遗憾,说“小木匠”没了。
我父亲给高表老送节礼,一直送到他去世,年年如此,节节不空,哪怕礼物少、也会上门去看看,也就是一种探望吧,都成了习惯。
那时老一辈的送礼、回礼,更是一种感情的沟通,以至于高表老次次都对父亲说,再来可别带东西了,你孩子那么多,家里也不宽裕。
父亲口里嗫喏答应,隔年继续如是,行礼如仪。
岁月无声、人间有爱。一包包果子、一段段土路,来来回回,反反复复,记录了这对忘年之交、人情世故。
当年,父亲和高表老共同经历的那一段血与火的往事,经年累月,演化成了老一辈、少一辈的交情。
5.表老要给我打造了一张婚床
后来,大郭庄我两个舅姥爷都去世了,父亲每次再去那个庄,就直奔表老家了,爷俩整上几个菜,喝点闲酒、聊聊闲天,聊天中,自然少不了我。
表老对我一直疼爱有加,除了想打算收我作“徒孙”外,他早早动员我父亲,在我五六岁时,就为我预备下了结婚用的家具木料,他以专业木匠的视角,巡视八集街里的木料交易市场,进行了各种木料的精挑细选和预处理。
爷俩早早地就把木料泡在了水里、隔段时间取出暴晒,然后再泡,这样反复泡-晒,保证木料几十年都不会变形。
后来我考大学走后,表老对我也是十分牵挂,知道我常年在外上学,工作肯定也在外头了,每次见了父亲,都问我何时结婚?随份子、喝喜酒,他是必须得来的。
我爱喝酒的父亲,听了这话,也是头大,因为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我在哪读书,也不知我有无对象,他从来不管我的学习、生活和工作。
有时我和大姐给他说了,他喝得醉醺醺的,也记不清、搞不懂,后面索性不管了。
遇到表老问,他喝下一杯酒,无奈地说,“这咱哪知道?他每次回来、都匆匆来、匆匆走。”
气得表老放下筷子,训他,“有你这样当爹的,是事不问?”
后来,我去大郭庄,找高中同学潘文玩,村口遇到了晒太阳暖儿的表老,我喊了一声“表老”,他有点不认识我了,我一说,是街南头、铁木业社的,再提了乳名。
老爷子马上想起来了,紧紧攥着我的手,不撒把,热情的眼泪都下来了,哆嗦着,非把我朝家里拽,让他好好瞅瞅我
再后来,我父亲再去送节礼时,老爷子对我一通夸。
那时,他已年过八十了,脑子还清楚,但精力不济了。
自从遇见我以后,他下定决心要为我打造一套好家具,啥时结婚啥时用、不结婚就放着。考虑到他年事已高、干劲十足,拄着拐棍一趟趟朝我们家跑、让我父亲赶紧在院子里腾地方,他要带徒弟给我做结婚家具。
而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,对象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,又想到我即便结婚,也不会在家生活,我们家一商量,决定请高表老利用木料打造一张硬板床吧?遂了老人的心愿。
接到任务后,老爷子精神头来了,虽然拿不动工具了,他还是强撑着身子,指挥着几个徒弟,花了十来天,精心打制了一张婚床、两个床头柜。
2004年,我结婚时,就用了那张大床和床头柜,这套组合是高表老和我父亲忘年交的见证,也是两代人的共同回忆。
每次我回到老家,躺在那张宽大又舒适的硬床上,心就十分安稳。
想起父亲带着我,一次次步行到大郭庄送礼的情形,仿佛就在眼前。
苏北老家,人穷情分厚,乡土生活,如同一抹浓酽的基调,一直植根在我的记忆中。
表老和我的父亲都不在了,但婚床还在,40年前的回忆如影随形。
6.后记
写这个故事的时候,还想起了表老的孙子,替我打架,在八中校园罩着我的有趣往事。
高一时,我们班是最乱的,学风差,班里人之间、和社会青年之间,经常打架,学不安生。我因为是街头长大的,自带标签,虽然人老实、不惹事,但也经常被人追打。
有一次和街里社会青年站立两排,楚河汉界泾渭分明,准备打架。
剑拔弩张之际,一个瘦高个、胸脯和膀子上都有刺身、满脸凶相的家伙,从对面招呼我过去,我有点害怕,怕他单挑我。
打吧,肯定打不过;不打吧,在众人面前没面子。心里打着鼓,硬着头皮过去了。
结果他一把抓住我,喊出了我的乳名,问我,你是街南头大铁炉子家么?
我说是的。
他凶神恶煞的脸,突然笑了,说,“我是大郭庄,你二哥。老木匠家的。”
一下子烟消云散了。他让我赶紧回去学习,还指着我,对他一帮兄弟恶狠狠地说,“草根是我的亲弟弟、祖孙三代半辈子的交情,你们以后打架不准碰他,谁要碰他一根汗毛,老子剁了他。”
当时,高二哥在街里打架还是很有名的,有他这句话了,我后面读书生活就平安了,都知道他是我的后台,罩着我。
再后来,高二哥当兵去了。
前几年在老街见到他,已经复员多年了,长年在外打工,满身的沧桑。
我有时想,如果我和高二哥仍在老街,老街如还是往年的生活节奏,我们还会保持祖辈们的感情和交往么?
这真的是一个问题。
可叹岁月匆匆,一去果真不回了。